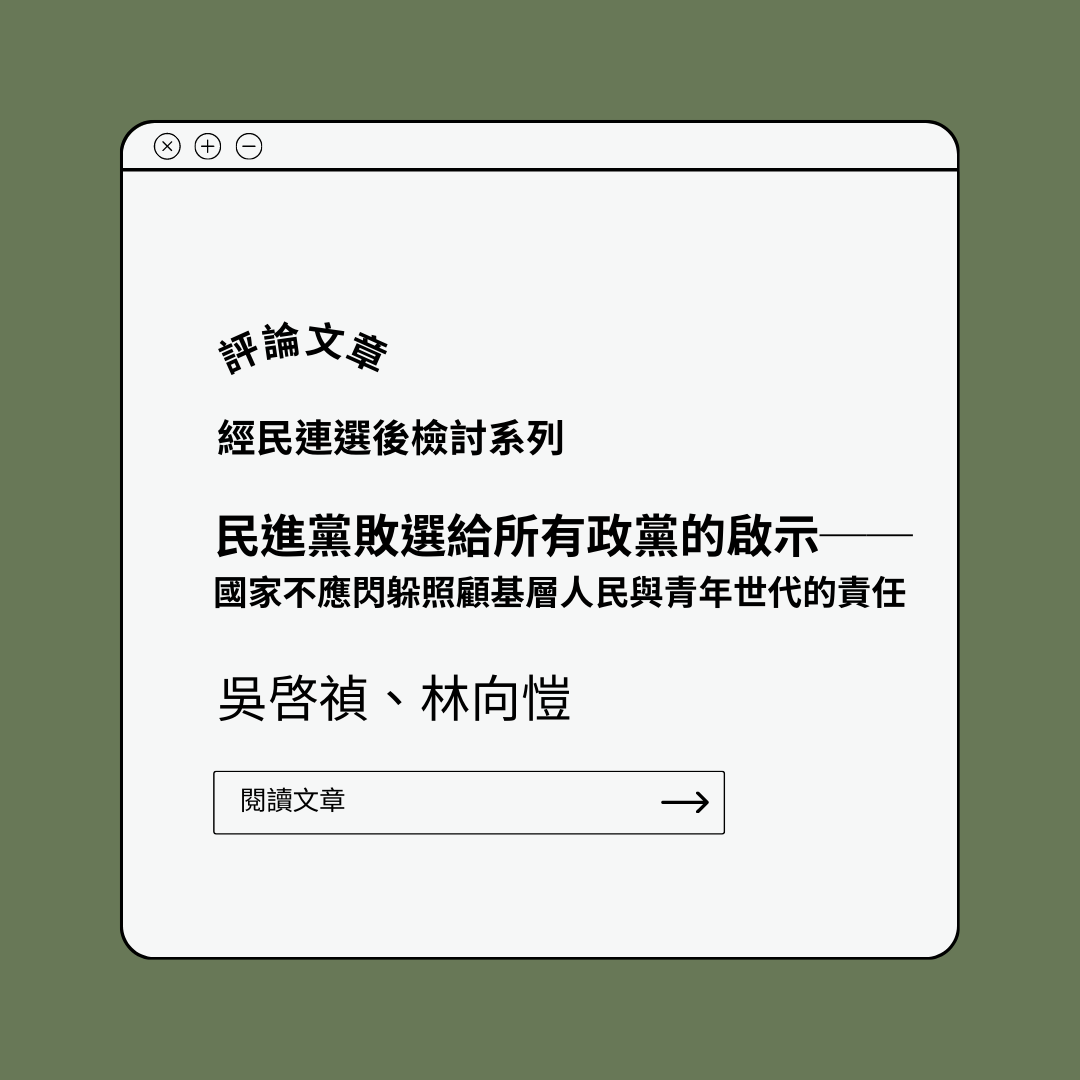◧ 經民連選後檢討系列一
文/吳啓禎(經濟民主連合智庫經濟社會組共同召集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博士)、林向愷(經濟民主連合智庫榮譽顧問/台大經濟系退休教授)
原文刊載於〈上報〉:
民進黨敗選給所有政黨的啟示──國家不應閃躲照顧基層人民與青年世代的責任
我認為這次民進黨大敗最大的問題,是因為年輕人的支持度下滑得非常低… 綠營完全執政8年,年輕人支持度還下滑,選舉結果就是反映出「年輕人給民進黨政府一個教訓」。所以民進黨如果要重視現實的話,一定要照顧年輕人,找回年輕人的支持… 所以接下來民進黨勢必要給青壯世代一個滿意的答案。
~ 報導者(2022-11-27),《野島剛:民進黨不是輸給藍營與中國,是輸給自己》
… 每到選舉之前,民進黨的候選人就會拼命打年輕人牌,去走訪同志酒吧、放搖滾樂等等。… 矢板明夫直言,但選舉一結束,民進黨就把年輕人的訴求拋到腦後。對高房價、薪資低等問題,並沒有下決心去解決。導致很多年輕人有一種被欺騙了的感覺。
~ 自由時報(2022-11-28),《矢板明夫列出問題提醒:討厭民進黨的人若越多 可能被中國見縫插針》
最近甫結束不久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完全執政已逾六年的民進黨大敗。有分析指出,此次選舉流失三百多萬票。選後第一時間,蔡英文總統辭任黨主席以示負責,民進黨成立敗選檢討小組,不旋踵即羅列十五項議題,似乎觸及各項層面。整個檢討活動至日前的第三次檢討會議似乎告一段落,召集人最後總結敗選最大原因,是「政策溝通與宣傳操作不當,選舉中的陸戰與空戰需加強與整合」。
正當執政黨將敗選歸因於選戰技術層級時,主計總處發佈最新國民所得統計,其中一個數字,對民心向背提供一個窺見窗口。這個數字是「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率」創下有統計(1981年)以來的歷史最低水準43.03%。
一個數字道盡台灣30年發展軌跡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總體經濟指標與數字,從中可以辨識出國家發展路線與社會階層分化狀況。台灣官方統計中的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率,國際間通稱為「勞方所得份額」(labor income share),或者更簡要的「勞方份額」(labor share),其概念是全民共創的GDP經濟果實,在扣除政府課徵的「生產及進口稅淨額」之後,在勞資之間的分配。由於尚未涉及到所得稅課徵與社會政策的重分配,是謂「初級分配」(primary distribution)。資方所得份額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OECD)的資料庫中係以「營業盈餘與綜合收入毛額」」項目為代表,此項目在國內官方統計中拆成「固定資本消耗」與「營業盈餘」,因此須將後兩者加總起來,方能回復到代表資方所得份額的概念數據(見下表)。

換言之,GDP的初級分配有三方:勞方薪資、資方利潤與政府收取的生產及進口稅淨額。表一清楚顯示,勞方所得份額在1990年左右來到高峰,於90年代後期開始明顯萎縮。同期間,生產與進口稅淨額占GDP比率也從1990年的高峰9.5%,縮減至今剩約一半水準。顯然,資方是唯一贏家,在勞方所得份額創下新低的同時,資方所得份額來到歷史新高52.3%
相較於1995年,勞方所得份額萎縮了GDP七個百分點,這代表什麼意義呢?以目前GDP超過新台幣20兆的規模,等於一年有1.4兆從整體受僱者薪水流失到資方口袋。若以目前工業及服務業全體受僱員工總人數817.3萬人,加計公部門工作者(公務員35.7萬人,各級機關約聘僱12萬人),則約略等於平均每位受僱者每月流失1.3萬元的薪水,對青年與中低薪族群來說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國家財富「藏於富民」,非「藏富於民」
經濟果實在勞資之間的流動趨勢,很大程度說明了台灣1990年代後期以來的低薪化、工作貧窮,以及財富過度往少數人集中(「藏於富民」,非「藏富於民」)的狀況。另一方面,政府利前稅(即生產與進口稅淨額)占比的急速縮減,其實並非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的常態,而是台灣所選擇的發展路徑所導致。
全球化時代,各國普遍面臨類似台灣的勞資分配趨勢為一耳熟能詳的主流說法,但事實上鮮少有國家像台灣如此嚴重。OECD與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於2015年聯合發布一份報告,主題便是針對各國勞方所得份額縮水提出警示與分析。報告中某些國家資料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以長時段為尺度的話減縮趨勢比較明顯。但若以1980年代以降為主要觀察時段,如本研究所整理的下表所示,與台灣相較之下,各國波動幅度其實相當有限:歐洲國家勞方份額減縮幅度較大的時間為1980年代,90年代即大致持穩(英國除外,其勞方份額減縮時間延伸到90年代中期之後才穩定下來),瑞士甚至出現微幅成長,打破上述全球化趨勢迷思;美國勞方份額減縮時間主要發生在2000年以後,但不算激烈;日本相對持穩;韓國勞方份額原本落後台灣,但近十年已後來居上、超越台灣。

市場面因素與制度面因素,全都不利於台灣受僱工作者
顯然,1990年代以降台灣勞方所得份額的縮減程度在國際間尤顯激烈—為什麼?上述OECD與ILO的聯合報告針對各國現象提出多重因素解釋,大致可分為市場面與制度面等兩大面向。市場面因素包含產業結構趨往資本密集度較高(即總要素生產力提高與資本深化)、低薪國家加入全球化競爭(要素價格均等化發生作用)、資本外逃與威脅(關廠、擴大引進外勞等)、金融化(裁員、壓低薪資支出以美化經營績效,取悅大股東與投資人)等。
制度面因素則包含勞動市場制度(如有無最低薪資立法、失業失能給付與涵蓋率是否足夠、產業公會與工會組織化程度、勞資協商機制、職業訓練系統等)、產品市場規範(如有無針對進口品生產時的勞動、安全、環保等管制)、公營事業規模(政府容易進行薪資管制的勢力範圍)、福利國家完善程度(減緩勞動商品化)、政府支出規模與規範(如防止低薪或外勞使用度過高的廠商得標)。實證研究結果指出,所有制度面因素的重點,在於形成勞方面對資方的薪資議價能力,這是影響勞方所得份額變化的最主要因素。

上述市場面與制度面的可能因素,為我們提供一個有如check list的判斷工具,可以說幾乎所有不利勞方的因素在台灣一應俱全。基本上市場面因素較為我們熟悉,制度面因素較為隱晦(跟我們的政治系統長期打壓工會與勞動權,以及勞動保護與福利體系滯後發展有關)。圖一所顯示的時間歷程,勞方所得份額在剛解嚴後開始民主化時期,大幅躍升至歷史新點。隨後隨著資本外逃、台商西進、外勞引進的不斷擴大,勞方份額迅速下滑,1996年李登輝政府提出「戒急用忍」政策,但成效不彰。2001年陳水扁政府對西進採取「積極開放」,恰巧也是勞方所得份額與資方所得份額出現「死亡交叉」的時點。之後勞方份額大概維持在44%-46%區間中起伏。2016年蔡英文上任後幾度向資方進行加薪喊話,且每年調整基本薪資,加上2018年美國前總統川普掀起對中國的貿易與科技制裁,刺激台商加速撤離中國,部分回流台灣。整體國內外的市場情勢似乎讓勞方所得份額出現向上契機,不料最近這幾年下探新低點。
到目前為止似乎可以做個小結,那就是光是市場面因素不足以支撐勞資之間有一個較穩定且合理公平的分配。官方以及先前某些國內相關研究認為,產業結構的資本深化造成勞動生產力提高速度快過薪資調漲–這類看法基本上不具制度面與國際視野。試問:台灣整體經濟的資本深化程度,會比表一中的先進國家來得高嗎?可能性殊難想像。所有制度面因素,對台灣受僱工作者不利,才是問題核心之所在。
設備投資是將本求利且有回收機制,但是教育投資呢?
台灣官方統計將資方所得分列為「固定資本消耗」與「營業盈餘」,前者即會計帳中針對生產設備所列舉的「折舊」項目,為資方從獲利中分期回收前期投資、政府為鼓勵擴大再投資而予以免稅的款項。從固定資本消耗占GDP比率的逐年擴大,來推估台灣產業結構朝向資本密集發展乃常見的立論分析。然而,全球化時代各國與台灣不僅資本密集度提高,人力資源的養成投入成本也大幅增加,而後者的報酬只有薪資,沒有「教育資本消耗」可回收個人與家庭為投入職場的技能準備投入。
況且,薪資除需支撐基本生活開銷之外,工作者還肩負了結婚成家、照顧長輩、養育下一代與儲蓄養老的功能責任,否則整體社會的再生產循環將告中斷,無法永續。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者即預言,如果薪資報酬一再「被壓縮」,接近維生水準,工作者將無能力生育下一代,隨之將發生人口減少現象—這項預言正是台灣的現在未來進行式。古典預言的下半部是人口一旦開始減少之後,由於勞動力短缺所以將帶動薪資上漲。這部分很可能不會發生在台灣,因為不分藍綠政府因應勞動力短缺的方式,都是擴大引進外勞移工(最近則是企圖引入更多外國中高階技術人力),持續壓縮整體薪資水準。
從個人教育投入的回收與投資未來世代的角度來看,低薪化、工作貧窮與整體勞方所得份額的過分縮減,對台灣的工作者顯得特別不公平,理由是與國際相較,國內個人與家庭對於教育的支出投入,不管是時間或金錢,都較先進國家來得更高。首先,在學唸書為未來出社會工作做準備的時間,台灣就遠超乎絕大多數國家。以2020年為例,國內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之人口比率(36.9%),較OECD國家平均值(33.0%)為高;專科教育程度之人口比率(15.4%),亦較OECD國家平均值(7.2%)高出逾兩倍。
其次,在台灣,大學及以上教育系統已呈現階級固化、階級複製與逆分配效應。有愈來愈多的研究指出,在台灣擁有優勢家庭背景的學生進一流公立大學的機率遠大過一般與弱勢家庭,而公立大學享有較多國家資源補貼,不僅學費較便宜,未來出路與收入也較佳。然而在3:7的公私比(含技專院校的大學部日間部在學學生數)結構下,就讀私立大學的學生數不僅較多,且許多出身自中間與弱勢家庭,通常需要申請貸款及同時工讀才得以就學。在學時負債日漸沈重,畢業後迎面而來的卻是低薪工作。
台灣青年三部曲:高教陷阱、工作貧窮與結構性負債
依循體制路線前進卻陷入「高教陷阱」與工作貧窮,是當代許多台灣青年共同的生命情境,之所以如此,其實非關乎個人努力程度,而是一環套一環的制度結構所導致。例如以整體國家對於高教系統的相對投資來說,台灣與OECD國家平均值差不多約GDP的1.4%(2018年數值),但是OECD國家政府平均投入約GDP的1%,其餘0.4%由個人與家庭承擔,台灣則恰巧相反,以致政府高教支出水準居OECD國家之末,人力資本形成的重擔落在個人與家庭。林宣佑(2022)指出,台灣每位公校生每年平均獲得的公部門補助為新台幣99,972元,私校生為34,897元,兩者相差近三倍之多。在公校生家庭社經地位普遍較優勢而私校生普遍較弱勢的結構下,偌大的國家補助差異無異加深了「逆分配」的階級固化效果,使得對很多人來說高等教育不僅不再是階級翻身的機會,反而是債務陷阱。尤其是畢業後低薪化的勞動市場,個人與家庭的高教育投資得不到合理報酬,形成高投資低回報的雙重剝削。
此一結構性負債已經產生無數青年悲歌與家庭悲劇。諸如日前立委所揭露的「自就學貸款開辦以來,已有5萬多筆因積欠學貸而遭銀行聲請強制執行的案件數」。 以及今年夏天爆發的柬埔寨人口販賣事件,受害的年輕人幾乎都是先前已債務纏身。此類事件相信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結構性問題的受害者不只是中間與下層社會,當國家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敗為發展主軸時—如國際健康研究指出,各種身心疾病會貫穿到上層社會,鮮少人可以倖免。
前面提到的影響勞資分配的制度面因素,重點在於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勞方在面對資方時的薪資議價能力,這可分狹義與廣義的不同尺度來思考。狹義上的較佳作法,是藉由強大工會與勞資集體協商機制,定期針對勞動條件與利潤分配進行談判。當談判陷入僵局時,國家需強力介入,協助建立勞資共識。廣義上,需有能夠確實幫助工作者「去商品化」的社會福利政策,也就是當工作者與家庭面臨各種社會風險時,國家有足夠的福利政策與資源予以協助,以避免個人無法維持基本的尊嚴生活或被迫接受不合理薪資待遇的工作。這些狹義與廣義的支持性制度,倘若不存在或者支持力道過於薄弱,勞動者選擇生活與工作的自由,其實是被剝奪的,無法不離家租屋,無法不接受低薪工作。而這正是台灣的現狀。
制度面因素在台灣之所以隱晦,有很多原因。其中的歷史政治因素是威權時代長期打壓工會與商會的組織化發展,加上污名化與遭錯置的社會階級意識,以致工作者普遍缺乏勞動權與團結意識。此外,解嚴後,台灣作為一個新興民主化國家,正透過政黨選舉競爭、建構福利國家制度之際,即遭逢新自由主義與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席捲,大量資本外逃西進,政府協助廠商引進大量外勞同時凍漲基本薪資長達十年作為因應… 這種種因素的加總,形成今天台灣勞動市場與薪資待遇的樣貌。
國家角色的設定,發展路徑的選擇
然而,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恐怕是國家角色的退縮,與其背後的意識形態。雖然從1980年代以來,小政府與放任自由主義在英美政治圈大行其道,但鮮少國家像台灣如此退縮。這方面我們可從兩方面來考察,即整體稅收能力與社會政策支出,這兩者攸關國民福祉、社會公平正義的福利體系建構,同時也是資源投入多寡的最具體指標。
首先,表三與表四呈示1980年以來台灣與主要國家的稅收能力。從下表(不含社會安全捐)不難看出,最企圖力行「減稅拚經濟」的美國雷根政府與英國柴契爾政府,在其任內的1980年代,稅收占GDP比率的變動其實微乎其微。將觀察時間延長至目前,這兩個國家的稅收占比依然呈現高度穩定狀態。在最近40年間,各國不含社會安全捐的稅收占比變化,唯獨法國(增加8%)、丹麥(增加5.5%)、韓國(增加3.3%)有較明顯的占比提升變化,其他國家大致持穩。唯獨台灣最為獨特:1980-1990年間有微幅增加,1990年為占比的高峰(19.9%),90年代後期劇烈下滑,2000年以後維持在11%-13%的區間;稅收占比減少幅度為所有國家之冠。(見下表)

其次,下表為將民眾所繳交的社會保險費用計入為政府稅收的四十年間變化,除英美外,各國普遍有明顯增加稅收占比的現象(如日本增加8.7%,丹麥增加5.7%,法國增加5.6%,瑞士增加4.7%,德國增加3.1%等),意涵著這些國家建構社會福利體制的努力,其中以韓國增加幅度最大(13%)。台灣目前官方資料僅可回溯至2005年,但已可看出,相較於蔡政府執政前夕,不僅無增加,反而是減少的(比較2015與2020數值,如下表)。

下圖為所有OECD國家最近兩年稅收占比(含社會安全捐)變化的圖示,哥倫比亞與墨西哥為敬陪末座的兩個國家。台灣雖然不在其中,但以2020年資料為準的話,台灣恰巧位居哥、墨兩國之間。此外,相較於OECD國家稅收占比平均值33.6%,台灣目前水準(18.1%)只略微超過一半。

隱藏在「輕稅簡政」政治修辭的背後靈:政府消極面對照顧人民的責任
以現代化國家而言,大概很難找出比稅收占比更能代表國家力量與角色的指標。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全球化時代中(特別需要國家介入來平衡過大的資本力量以保護民主社會,如多數國家之作為),國家角色在台灣獨樹一幟地呈現激烈退縮現象,此退縮不僅是相對於自身歷史與同時代其他國家,而且退縮到一個絕對性低落的程度。這並非「國退民進」,也絕非執政黨高層素喜吹噓的「輕稅簡政」、「藏富於民」,而是讓財團與富人階級享受超低稅率環境,留給台灣青年世代一個低薪、低保障、結構性負債、難以成家育兒、以及等在未來的孤老病貧的老年生活。
聯合國為計算各國國民所得帳提出了一個「四階段分配法」,可以做為我們進一步思考國人相對所得的分析架構。四階段分配法中的初級分配,也就是此文前面所關注的經濟果實一旦創造出來之後,在勞資之間的分配。同國家稅收能力一樣,對勞方而言,勞動報酬占比的縮減不僅是相對於自身歷史與同時代其他國家,而是已經退縮到一個絕對性低落的程度。儘管蔡政府上台至今六年多,基本工資年年調漲,但是在整體薪資調漲幅度持續小於經濟成長率的情況下,資方所得占比創下歷史新高。
請注意,分配議題的重要性在於它本質上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如生物演化的「紅皇后效應」,自己前進五十步不是前進,當其他人前進了一百步的時候,其實是相對落後五十步。同樣的,不僅是勞方所得占比,不僅是政府稅收絕對數字的多寡,當資方所得份額遠大於勞方所得、遠大於政府稅收時,儘管有加薪、財政收入有超收,分配的公平性還是受到傷害,公共政策所能動用的資源還是追不上時代與社會的需要。
從聯合國「四階段分配法」窺見台灣基層與青年慘狀
那麼,初級分配之後的三級分配,對台灣青年與一般民眾會不會比較友善?
- 第一階/初級分配:利潤在勞方、資方與政府利前稅之間的分配
- 第二階分配:社會政策中的現金給付
- 第三階分配:社會政策中的服務給付
- 第四階分配:可支配所得的消費與儲蓄結構
為省略起見,我們將第二階與第三階綜合起來分析,這兩階的加總亦即政府的社會政策支出。根據OECD定義,社會政策支出含括以下九種政策:(1)退休年金,(2)遺屬年金,(3)失能相關福利,(4)衛生醫療,(5)家庭政策,(6)促進就業計畫,(7)失業給付,(8)社會住宅,(9)其他,如疫情衝擊下的補貼等。
基本上,這些項目觸及到每一個人與家庭在生命周期當中幾乎必然會有的需求與風險。這些需求與風險,如果多數由個人與家庭自行承擔,也就是傾向「風險個人化」,則政府的介入程度乃至社會政策支出總和定然較低。而這些個人與家庭需求得到滿足的程度,通常則視市場發展,以及個人與家庭的社經地位而定。條件較佳者,可透過金錢等資源向市場尋求服務而得到滿足。較差者,甚至會負擔不起市場所提供的服務。因此,愈傾向風險個人化的社會,其階級分化程度乃至相對剝奪感就愈大,社會團結乃至政治穩定度也就較差。
反之,若政府設計並統籌治理相關制度,由整體社會來共同分攤上述九項民眾生命需求,也就是「風險社會化」,此即「福利國家」概念。福利國家愈完善,則含民眾繳交社會保險(如勞健保)費用的整體社會支出可能就愈大。一般來說,福利國家至少有兩大特色:一、具有所得重分配的功能作用(重分配的程度不一而足,視機制設計而定),如所得愈高者繳的保費較愈多,但所有人對福利服務享有同等的近用權。二、因此而打造的社會較平等,較無階級分化與歧視,有利社會團結與民主政治的運行,因此也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長遠進階發展。
有了上述概念基礎,我們接著來檢視第二與第三階段的國民所得分配狀況,這兩階相加起來,正是一國的社會政策支出水準,也代表了該國投入建構福利國家制度的資源多寡。下表所呈現的最新資料顯示,OECD國家平均社會政策支出為GDP的20%,法國、丹麥與德國高出平均水準甚多,日本與英美接近平均值,台灣為最低(11%)。從時間歷程來看,韓國雖然起步最差(1990年只有2.6%),但後來急起直追,目前已超過台灣。其他國家在過去四十年間社會政策支出均呈明顯增加態勢(荷蘭除外)。而台灣從2000年以來縱然有些微增幅,但增加很有限,在原本就薄弱的基礎上,看不出有積極面對青年與民眾需求的施政企圖。

第四階分配是探討個人與家庭可支配所得的消費與儲蓄結構。上述九項社會政策所涵蓋的生命週期需求與風險,在缺乏足夠國家社會政策支持的情況下,個人與家庭需運用可支配所得轉向市場購買相關服務,然而在普遍低薪情況下,扣除基本生活開銷後,還能有多少儲蓄去購買相形昂貴的商業服務與保險?
… 根據yes123求職網調查,我國39歲以下僅25.9%青年收入大於支出, 36.%收入小於支出,青年零存款比例從2019年15.4%,升高至今(112)年20.3%,零存款比例年年增加…。
最大的諷刺,無非是見政府高層經常誇口說,台灣物價低廉,且無通貨膨脹壓力,因此若用購買力平價法來計算的話,台灣國民所得水準可名列世界前茅… –這項說法至少存在兩大迷思:一、低物價不正意味著普遍的低薪工作,以及低廉用品的大量進口?如攸關餐桌食物的農產品與化石燃料?而後者,不正是打擊國內糧食自主、農民所得、綠能轉型的元兇?
二、房屋與居住是生活必需品,但目前政府所發佈的物價指數,並不包含房價,這項作法已脫離國際物價指數的編列方法。而在台灣,相對於所得的房價,偏偏是全世界最貴的都市區域。低物價低通膨,其實是迷思,是錯覺。
結論:
買不起房,在台灣通常意味著成不了家,也就沒有後續的育兒。綜合以上分析,不難理解為何當今台灣享有全球最低生育率。有些論點將原因指向時代價值觀念轉變,Esping-Andersen (2016)駁斥這類說法,其透過長期且跨國資料的研究成果指出,造成低生育率的原因出自國家過於偏袒資方,怯於保護廣大勞動社會,以及吝於投資個人教育與家庭政策的結果;扭轉之道不能只限於鼓勵生育,而是必須建構良好福利國家系統(包含落實性別平等)。
事實上,台灣不僅人口已步入負成長,目前工作年齡人口占比較先進國家為高的優勢也將轉為劣勢,屆時情勢對青年與未來世代會更形險峻。
對出身一般家庭的青壯世代而言,歷屆政府所共同營造出來的不友善環境,讓每個人必須努力求生存才得以稍微喘息,讓每個人沒有理由去信任政府,這樣的環境氛圍造成社會撕裂、詐術橫行與政治激烈動盪。事實上,無節制的資本主義經濟造成唯有有錢人才得以享有自由,與民主政治賦權給每一個人的機制之間存在永恆的張力。史有明鑑,唯有厲行平等主義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能夠有效實踐民主的承諾,讓全民共享經濟果實與自我實現的自由,所有有志執政的政黨焉可不查。